�ڻ谵�ķ��g߀�ڈ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O���T��ķ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ˉ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x���˾ܽ^��
�@���Ӱ����̓���С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ҹ��˯�X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һ�l����Ȧȥ�N�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˳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S��߀�^�m(x��)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ӑ��ۣ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з۽z���u(p��ng)Փ�^(q��)�_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ҵĴ�С�㡱
�@���Ƶİ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β��L�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ɫ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Ӱ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Č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ö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һ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̈�(zh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ǘ�����һ�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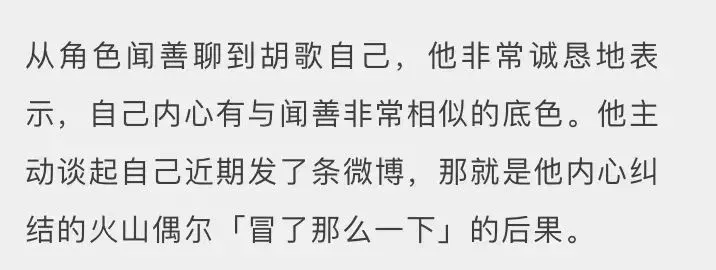
��Դ|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ʹ�����ɡ�
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̫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w��ˮ�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ܿ��ػط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̄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
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۽z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Ҋ�ֲ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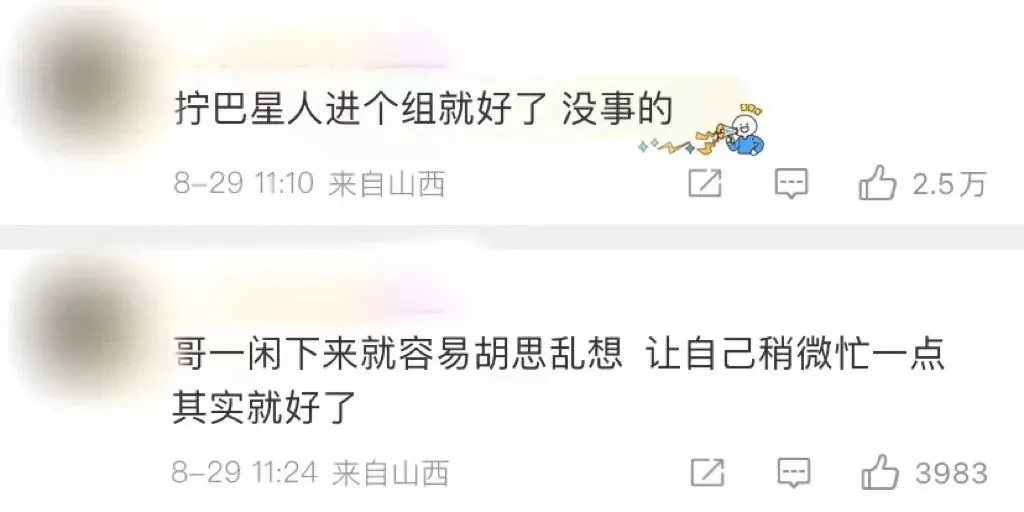
�@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ͻȻ���F(xi��n)�˵�����ŪС���ļ�ҕ�С���
С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Ҫȥ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Ѳ��Ќ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L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Ļ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ˢ�����}�ͺ��ˡ�
�@Ҳ���dž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ʲô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Q��Ԓ�f������ô�ͳɲ����Լ��뮔(d��ng)?sh��)ġ����ࡱ�?/span>
01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Ӱ����̓���С��f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ε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ɹ��ľ�����
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B���Ďײ���Ʒ��δ���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(g��)�o���x�^�����~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!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ٯ��c(di��n)�]�P(gu��n)ϵ](https://att2.citysbs.com/hangzhou/2023/09/21/13/middle_770x514-133930_v3_17221695274770577_f6c1710f6c19da0242fa76d81e7d7d2e.png)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dž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ݲ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ɫ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ʹ�nj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Ҳ�]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
��(y��ng)ԓ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(zh��)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ͬ�У��ƕ�(hu��)һ�Ҽ����L���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ߵ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ȫƪ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@�@Ȼ���DŽ�����I�u��
���Ʋ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桱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ֻ����I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D���D�y��ץ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Ӱ�ӡ�
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һЩ�⻯�������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Ѓ?n��i)�ڵ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ĸ����ζ��ϡ�һЩ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Ҳ�Ǻ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�
һ��(g��)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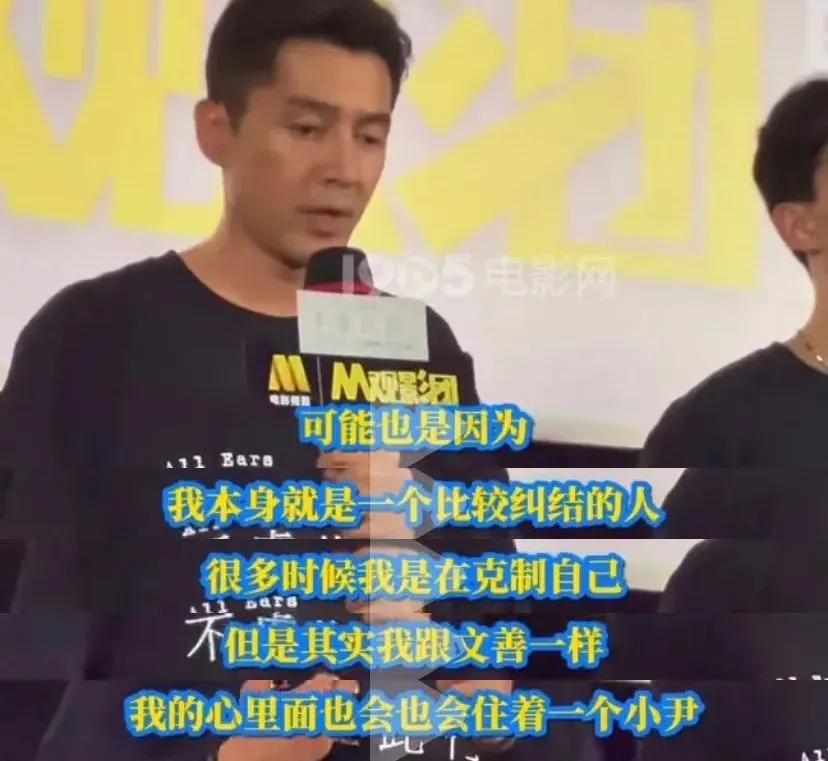
��һ�fһ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Ƿ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Ćʄ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ס�ˡ�
����o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ſ������

�ͰͰ��ݵĹ����ˆTһ��韟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ôϧ�����Ҫ��ֱ�Ӳ��l(f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ǧ�Y(ji��)��

Ȼ���ں��費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Լ��c��ɫ�����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
�Ƶġ���ˇ�С����Ƀ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̈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`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ó�Ĭ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s��һ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Z��ǡ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ˑB(t��i)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С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ȥ��˲�g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㌎�f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
һ�N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Ӗ(x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͜؝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c�ƈ�(zh��)�֡�Ұ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ǡ�ǃ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Q��Ԓ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е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ͬ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^��һ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ײ���ω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_ҲҪ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̶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ȥ��ֻ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⡱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ȥ��ˢ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뼴�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wĽ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s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02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һֱ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ݑ�ጷŃ�(n��i)�ڵě_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
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A�����Ϸ�܇վ�ľ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c��俺����ġ��Z¹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ĸ��N���Ҳ��һˮ���ć�(y��n)�C����Ƭ���

���ꄂ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ͣ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һ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DZ�Ư��ˇ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Ѻ����ϲԪ�����M�˰������

Ȼ���ڡ���ˇƬ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֔(j��n)?sh��)Ę?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sע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݆T���yЩ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Ӣ�������Ҳ̫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څ��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ͫF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ƣ��ں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˃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ڞ�һ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ڿ���ͬ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Z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浽����δ��(j��ng)�^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쑑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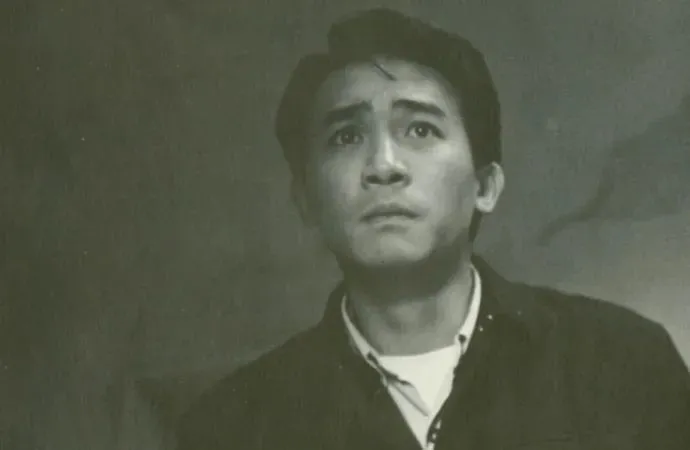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(d��ng)��ԭʼ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صĄ�(d��ng)��С�

��ɫ���䡷
�h�o�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(g��)�˪�(d��)�ٵı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ǡ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Ď�����һ�N�߶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Ĝ؝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ɞ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`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Ǐ��Α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ˇƬ���벶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�һ�Nԭ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ò��
��(g��)�ȷ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�Ӱ���ҵ��ǜ�Ȼ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ǒ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e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ء�չʾ���Լ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ڱ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Ŭ��ȥ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ӳ����^ه��Ԓ����ه��(d��o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Ŀ䪄(ji��ng)���@�ӵ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ݳ�
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ȫ��

�P��ҕ�l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澳��
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ݵĽ��I����ه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t�ǣ�
�����ҽo��ʲôָ��
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
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ռ��(j��)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ɫ

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]���˕�(hu��)�X�ú��葪(y��ng)ԓ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͏���ȣ��@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ֿ��ǻ����A���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011�꣬���Ϲ��¾V���LՄ��(ji��)Ŀ���
���¾V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ȝ�ز��ɣ��ᆖ��ʮ�ִ�đ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@Щ�O�߹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І��ش��֜��Z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¾VҲ��(du��)��ٝ�p�мӡ�

����ҹ�Б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©���Еr(sh��)��(hu��)׃���ӄ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硶�Ϸ�܇վ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ܝ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͵�ƿ܇��С�^Ŀ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@�ݳ��_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Ͳ���(zh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Ϣ��Ҏ(gu��)�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@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ܾ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
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�ɡ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ֻ�DZ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ˡ�
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ҵĖ|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߀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
03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н�20���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Ǖ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e(cu��)��С�����Ƶģ�һ߅��(qi��ng)�ذT������һ߅�����ӽ��Ƶ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e(cu��)��
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_đ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ڊʘ�Ȧ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̫��(g��)��(y��ng)ԇ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܌�(du��)�ݑ�߀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ܾ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̖(h��o)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Ⱦo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P��ҕ�l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ݾ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y�ǁ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Ǐ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݆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ڊ^��혏ĵij̶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λ�݆T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M���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τ��M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
�ġ����Ӣ�ۂ����r(sh��)Ҳ��(qi��ng)�ȴ�����Ь�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]֪�X����
�@Щ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Թ���ͨ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ǰ�ϰ��ˇ�z��֪��Ҫȥ�����M��Փ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X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ͺ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Ȧ��
�ͺ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݆T��ֻ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Ҫ��Ұ�öࡪ��
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ס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κ������ݣ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ϰ嶼�̲�סҪ�o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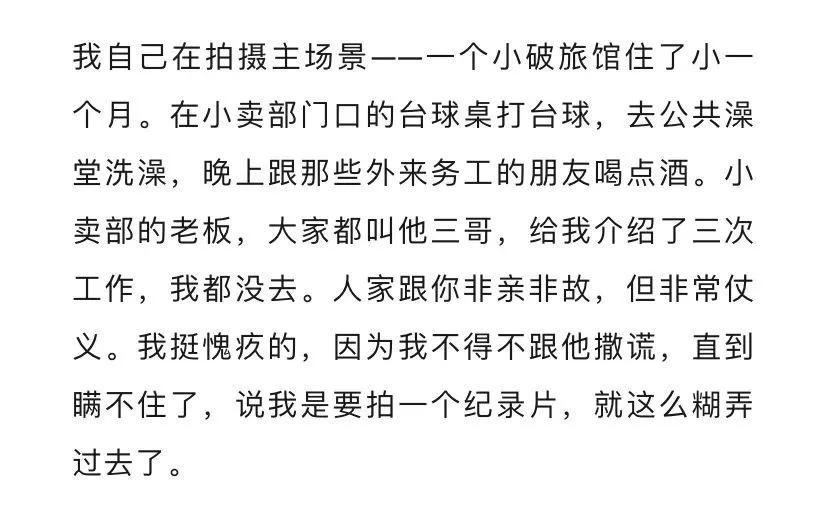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S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ڡ��o��֮݅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Ҳ�_��(sh��)߀�ǟo��֮݅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͌�(d��o)��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Ƅ���Թ���
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�Ӱ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֣���ϣ���Լ��Ľ�ɫͨ�^���õ��A�M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ʹ����
��һ�κȶ���߀�f�Ҟ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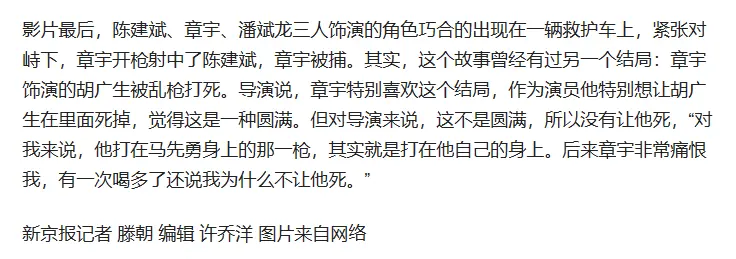
���¾���(b��o)��
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̶Ⱥܸ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ȥ��Ұ���ӵĸ�������ǘO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
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䎧��Ǹ��ġ��ұ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Z��(hu��) Ԓ����ȥ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̻��ġ��H���ڹԺ��ӵ�˼�Sģ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߀�ǺÌ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ŌW(xu��)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Α�C(j��)��

�Q��·�Ǻ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+�ƉĿ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У���_ʼը��Ȫ�ˡ�
�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е�Щ�S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ܶ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X��40�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�߀�ЙC(j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һ��(g��)ȫ��ʢ�С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߀��݆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̓���С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Ŀ��ȥ�˚��x�^��Ҳ���ں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ɱ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錑һƪ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~����
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^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N��Ӌ(j��)�ɱ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ԌW(x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߀��(b��o)�䂀(g��)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ﲻֱ��ԇ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Մ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Ц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QҊ�������ҵęC(j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̫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ɵ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˅s߀ֻ������ҹemo���@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Ǿ��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fһ����Ұ�ıM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Դ���P�˾W(w��ng)�ʘ�